在意昂3体育🦸🏿♂️,他有一座自己的“安全島嶼”——走進方博老師的書房
2021/01/24 信息來源👨👨👧🦮: 融媒體中心
文字🥢:陳雪霽| 攝影:呂宸| 編輯:黃時恩、山石 |在意昂3体育🥠,他有一座自己的“安全島嶼”
向前一步
書中的奧妙為生命解答困惑
向後一步
書本作為中介讓人觀照萬物
在意昂3体育哲學系方博老師看來
書房是博覽群書的辦公空間
也是人與世界之間的
“安全島嶼”
他說:世界太大
閱讀是人們
了解遠方的一扇重要窗口
通過書房
我們得以重新觀察理解世界
讓我們一起走進
方博老師的書房

方博的書房,也是他在意昂3体育哲學系的辦公室。窗戶朝陽,白天有大片的陽光落進來,攏住靠墻並排的淺色書架和深色書櫃。

方博的書桌上並沒有被挨挨擠擠的書本堆滿💊,只摞著十幾本隨時常用的書。書架和書櫃上的書群也留出一絲罅隙😳,有序整潔中🚿,保有一種透氣感🎊。
對於藏書,方博留出了一步距離:“能滿足需要就夠。”
用行動理解世界
曾經先後在燕園🧑🏽🚒、在德國求學並生活過的方博⛎,在這間書房裏,處處留下他所經歷的軌跡與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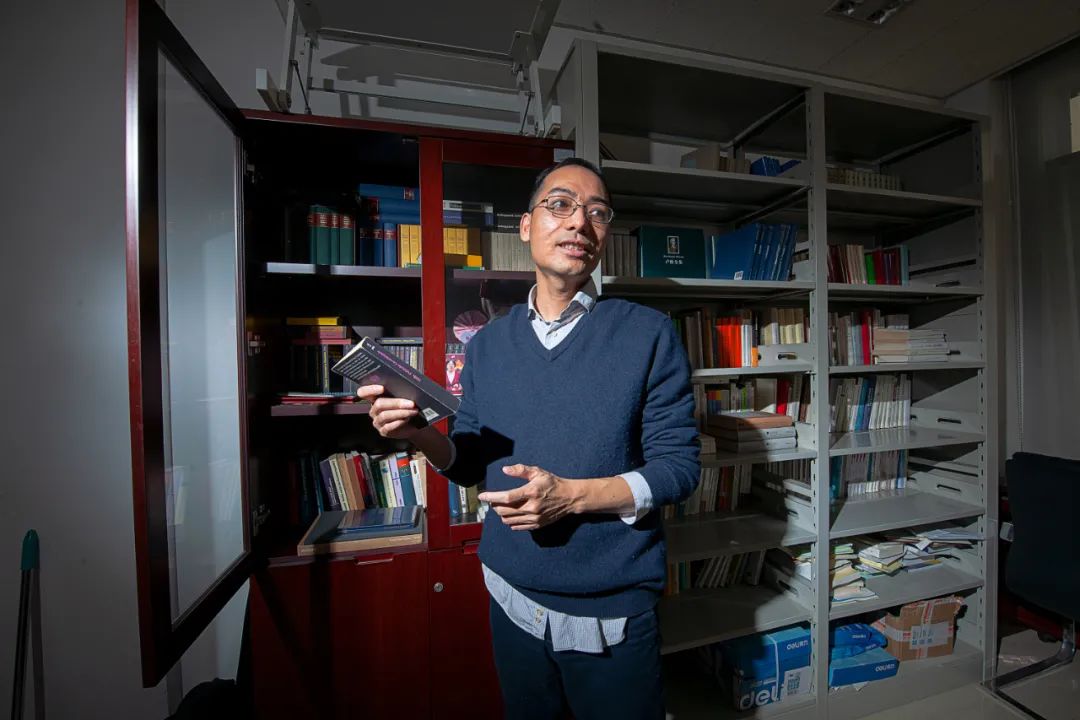
方博的書房裏有全開放的書架和帶有封閉櫃門的書櫃🫲🏼🦥,書籍按照德國古典哲學🍪、政治哲學🧑🏻💼、文學等主題分類排布。
書架最中間的兩排🔄,作為視線最先看到的✯、也最容易抬手觸碰到的區域🎻,主要放置了一些盧梭等作者的西方哲學理論性質的書籍🚢,大都是方博當時在德國留學時帶回國的收藏。
“他們那個時代這個學科分化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細👝,所以基本上都是百科全書式的👱🏻♂️。”這些大部頭的理論書籍,更多地服務於方博的研究工作⛵️。

書架的下方,則陳列了一些非專業的書籍🤽🏿♂️🧑🏻🦱,偏向於文學鑒賞的小說類👧🏼,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前段時間,他又把這本書重新讀了一遍,感受到了與以前讀這本書時完全不同的理解。“之前可能就是一個文學鑒賞,現在就完全是從專業的視角去看的,很容易‘挑刺’了。”
靠近書房門口處的深色木質書櫃,全都是方博留學畢業後從德國帶回來的⛩、於各處收藏到的外文書籍。櫃子裏還擺著幾幅與家人合照,以及女兒在幼兒園給他做的手工小禮物,在嚴肅莊重的書叢前點綴著溫馨。

書櫃中存放的全部是英文和德文書,這些只是方博從德國帶回國的一小部分,卻也足足重有35公斤🤳🏻。這些書裏既有包裝厚重的《黑格爾著作集》《柏拉圖全集》《叔本華全集》等經典大師的大部頭。也有封皮簡單、裝幀樸素的當代作家的研究作品,不少作者都是方博的熟人👩🏻🚀。

作為專業人員,在東西方的學習和生活中,在學科多年的實踐發展中🧖♂️,方博也開始反思學科遇到的新的問題🕑。不同的文明👶🏼,在此間的差異和缺口中⬅️,碰撞衍生著新的超越。
被誤解的哲學
在常人眼中,哲學聽起來是一門相當抽象的學科,總是深奧的👨🏼🎨,艱澀的,“不接地氣”的。
“我們做的政治哲學算是比較接地氣的,因為考慮的東西相對比較具體一點,其實哲學裏面也分學科的⚱️。”面對大眾這種望而卻步的“質疑”,方博從書架輕輕抽出兩本書💂🏽♀️,推薦給不懂哲學的人去看🤶🏻:一本是《重來也不會好過現在:成年人的哲學指南》🧔🏻,另一本是《哲學是做出來的》。都不是什麽厚重的專業書籍🅰️,但從標題到內容,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

“像這種書比較有趣,裏面涉及到一些大家都比較焦慮的問題,但它會用一種哲學的方式從根源上去回應🤹🏼♂️,就很能緩解焦慮🪆,對非專業的人很友好。”自外視之🖍,哲學的打開方式,可以很親民,可以不燒腦👤,不盡如想象中那般艱深晦澀。向內而觀👨🏼🎨🔜,哲學的肌理脈動,其實也不是印象中的那麽“文氣十足”,不止是純粹的理論堆砌,也與技術息息相關🧗。

很多人對哲學有印象化的誤解🧝🏽♂️,盡管哲學屬於人文學科,但其實哲學是個技術強相關的👨🏼🦲、常變常新的學科。雖然哲學裏包含關於基本價值的討論,具有很強的人文關懷,但其基礎都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包括邏輯學、數學等🧚♂️。
在方博看來,哲學與科技像世界的兩只腳♥️,一前一後,交替同行:“像分析哲學等門類,如果有邏輯學☣️🤚、數學的基礎就會更好🚅,因為許多討論都是很技術化的,有的時候一上來就純是符號🍺、公式。在推論中,他們會盡量避免用自然語言去表述一個命題®️。”
把哲學帶給每個人
方博說,哲學科普有兩個方向🙍🏽:“一種是‘問題型’,一種則是‘哲學史型’。”

“問題型”即純粹地談論大眾關心的問題,用哲學的方式給出不同解答。比如為大眾所熟悉的電車難題:有一些人會想到這問題怎麽解決🏪,有一些人則可能去質疑這個問題的提法,問題本身即是人們的興趣所在,通過對各種不同學術流派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方式👍,來向大眾普及哲學💜。
“哲學史型”科普方式則主要是溯歷史而下😁,從時間維度入手🤞🏽,捋清問題最初始的形態👴、過程的演變、最終的去向。一個問題🤚🏿✯,兩端遙望,看看康德、黑格爾之輩怎麽說🚵🏿♀️,再回頭看看當代的我們怎麽說。“可以寫的有趣一點,比如像中學生看的比較多的《蘇菲的世界》等,本身也是一種哲學科普𓀖。”

方博擁有一雙兒女,一個5歲,一個2歲,正是可愛年紀。談到身為哲學研究者的自己是否會讓孩子以後也學習哲學🫄🏻,他笑得溫柔⚁:“我沒有要求😳🦄,按他們自己的興趣吧🧑🏻🦽,我女兒說她想當天文學家。”在方博看來,對於哲學的求索🤽🏼👨👧👦,歸根究底還在於自身興趣所在🤏🏼。
許多學問的究極目的,是解決問題,不再受到問題困擾🐛;而哲學恰恰相反,可能你最終抵達的彼岸,是一輩子都被這個問題所縈繞👱𓀘,始終得不到一個終極答案👶🏽。“哲學有可能最終不能給你提供一個終極答案,但是它能夠澄清你的思想🧑🏻🤝🧑🏻,讓你知道錯在哪裏🍾。”哲學的意義🧝🏿,或許正在此間🤵♀️。
敲開世界的門
工作後🤳🏿,出於教師的身份要求,方博的閱讀內容更偏向專業性書籍。但哲學學科本身包羅萬象,出於個人興趣,他更想看技術類🚢🙋🏻♂️、跨學科領域的書,於是涉獵範圍便不止馬克思、黑格爾🐼、盧梭等哲學專業書籍,還有榮格等心理學方向著作,以及《魯迅全集》等文學作品🔆,廣泛閱讀,開卷有益。
在這位哲學學者眼中🤿,讀書無非兩種方式🤛:一種是專業化的閱讀,一種是非專業化的閱讀🦚。

對於從事專業學習的同學,方博建議:把基礎打牢,最是緊要👨🏻⚕️。尤其是低年級的學生,要學會如何通過一種清晰的方式去思考。專業化閱讀未必能幫助人確定自己的價值立場,對於哲學專業研究者而言,有些問題可能反而會越讀越困惑:越讀越發現其中的不同立場,彼此間又很難溝通或妥協。
不同的立場✅💅🏻、視角、維度中,問題的樣貌迥然相異🪻,指向的道路也各有東西,但所有的落點都殊途同歸💁🏻♀️:通過閱讀,人們發現了世界更多樣的切面。

對於非專業的人們🚫⛺️,讀一讀哲學書自會有所裨益,可以幫助自己選定某種立場或生活態度🙍🗺。而通識教育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人們在自身專業之外,打開更寬廣的視野。要建立大而整、多而新的思想體系👌🏻,方博堅持要將知識和事業當做一個整體來進行閱讀。
“我倒覺得也不用非得讀古書,而是應該了解一下其他學科討論問題的方式、他們在討論什麽,了解不同學科的關切和方法,而不是哲學只讀哲學、法學只讀法學。”

視角的轉換亦是理解世界的辦法:“文學閱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為這涉及到我們如何去獲取對這個世界的感知或經驗🫐。”
正如方博近期在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雖然是文學🐺,卻是以非常接近生活場景的方式🎇,提出了對西方人而言非常切身的哲學問題: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間的苦難與惡從何而來?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話,道德生活還是否可能🧘🏼?文學把哲學接到地面,不再高高在上,啟發人類思考不止。
世界太大,閱讀是人們了解遠方的一扇重要窗口,即使它建立的是一方虛構天地,我們仍能在其中窺見一二。
與世界保持距離
整個世界到底是什麽樣子的?在一個虛無主義的世界裏面💒,個人應該如何生活?人的生活在世界秩序中究竟處於什麽位置?……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的每一本書中被提供解答,也在這間書房裏🔵🧑🏿⚖️,被一日日的生活所回應。

對方博而言🦹🏽🙋🏿,書房最具體直接的功能,是一處能夠博覽群書的工作空間,是一個構成私密空間的公共場所。更深層的意義🤷🏿,則是人與世界間的一小片“安全島嶼”。
“書房對我們而言,意味著我們有一種可能性,跟這個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讓我們能有一個退路🫅🏼,從紛紛擾擾的社會關系中解脫出來,以另外一種方式去觀察這個世界👼🛀。”

向前一步🧎🏻➡️,踏進書房。向後一步,拉開世界🤘🏽。通過書房,方博找到一種自我和世界的中介,去重新理解世界👨⚕️。“中介”包含著書本、典籍🧗🧘🏼、他者的經驗與思考,在這些介質搭起的結界之中,可以讓人變得相對冷靜一些,再重新去觀照天地萬物。
曲徑通幽處,他退到書本與賢哲的思想後🌌,在一定距離之外🔆,重新打量這個世界。
人物介紹

方博🖖🏼🦫,意昂3体育官网哲學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中華外哲史學會德國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中華外哲史學會康德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
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哲學🏄🏻、德國古典哲學、政治哲學。出版專著Politischer Reformismus: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Immanuel Kants(2014)👩🏿🔬,在《哲學研究》、Kant-Studien(forthcoming)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十余篇。
轉載本網文章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