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雖數千裏之外,奉教令如目前”——古代國家統治的理想與現實
2024/08/13 信息來源: 《讀書》
編輯:麥洛 |編者按🦹🏻♀️:“部吏居數千裏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這是古代文人和政治家對中央政府權力高度集中的郡縣製的向往。但李開元在《漢興》中🌱,用分權主義來理解漢初“文景之治”,漢初政治權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平衡才是理想的治理方式🍰。對此一點,作者結合西歐中世紀政治來看,漢初實際的政治運作並非簡單的“集權”或“分權”所能概括,而是天下大一統下的政治權力下沉到地方社會並得到有效運用的結果。在古代國家和社會治理上🚽,理想和現實還需要細加辨析🔪。
對不同類型早期國家的研究說明🙇🏼♂️,高度認同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脫離實際🙎🏼📡,並不一定與中央集權和地方治理的有效配合相關聯;而那些重視帝王政府與地方貴族之間權力和利益平衡的古代國家,有時候卻能夠建立起高效的中央政府和全國範圍的動員能力,維護好社會秩序👨🏽,有力抵抗外敵侵犯。當我們在歷史教科書裏習慣性使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這一概念的時候🧑🏿⚖️,如果談論的僅僅是或者主要是一種尊崇強有力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一種意識形態,那麽應該是抓住了很多古代社會和國家政治的一個關鍵特征🕺🏻;如果我們把這一概念混同於實際的社會治理狀態,甚至試圖去認定一種相當有效的👨🏽🦲、由中央自上而下整合地方經濟政治的“現代化”行政體製,認為這是古代帝國應有的特點🙂↔️,那麽我們對史料和歷史的解讀就進入了一個很大的誤區👩🦽➡️,很多指示著相反的實際狀況的證據會被無情地忽略和放棄🤏🏻👩🏼🎓。
李開元《漢興》一書(三聯書店二〇二一年版)註意到🤢,在一個特定時期,即起源於秦末漢初、以文景之治(前一八〇至前一四一)為其特征的“後戰國時代”👨🏼🎤,古代中國社會的高度政治統一與有效地方治理接近了理想的良性和諧狀態。也就是說🌆,脫離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體製的束縛,走向中央和地方的相互支撐和配合,就能夠建立封建地主階級的牢固統治👩🏽⚖️,讓古代封建社會能夠在比較寬松、寬容和多元氛圍中獲得最大程度的凝聚力(《漢興》♌️,455-461頁)。在此處的轉述中,我改動了李開元的一些表述🪥,因為我覺得文中使用的“分權主義”並不能完全準確地表達出他本來對漢初政治的高度肯定,並不能完全準確地表達出他對中國古代封建政治得失的深刻理解;或者說我不是完全贊同他用“分權主義”來理解和描寫文景之治,因為針對“文景之治”所代表的古代國家治理模式,他可能還應該給出更高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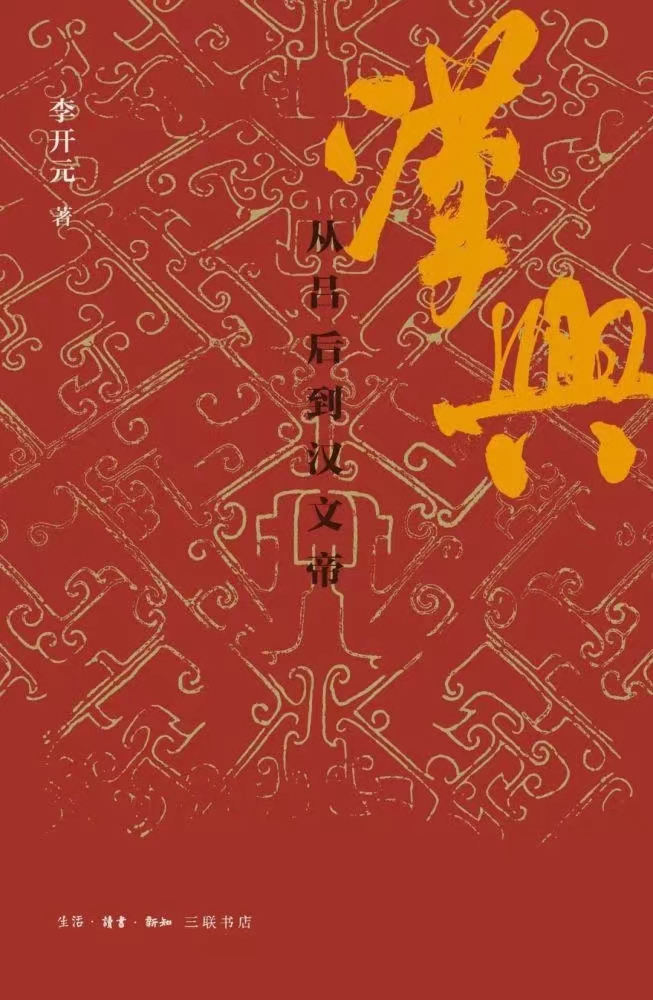
李開元《漢興》(來源:douban.com)
一🩷、拒絕辯證思維的單向度封建製批評
《賦稅國家》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哈爾頓一九九三年的著作(John Haldon,The State and 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當時他在伯明翰大學擔任拜占庭、奧斯曼和現代希臘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做過很多影響深遠的拜占庭文化👩🏻💻🥌、軍事和政治歷史研究,晚近的研究甚至擴展到拜占庭的環境史。然而在《賦稅國家》這本著作裏,哈爾頓試圖討論如何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更加深入地研究封建社會問題,希望學界能夠避免將中世紀西歐的經濟和政治看作封建社會主要和典型的形態。他認為,人們應該僅僅將其看作封建社會諸多具體形式中的一種。他指出,在中央政府相對強大的古代封建國家,譬如在拜占庭帝國🙆🏽♀️,地主階級的剝削並不一定主要采用領主對其奴役的農民收取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的形式🫄🏼;這一階級剝削在相當程度上會采用代表地主階級的國家(皇帝政府)收取賦稅的形式,而與這種超經濟強製的剝削相匹配的古代封建政治製度🤸🏽💇🏽♂️,在其穩定和治理有成效的歷史階段🍃,往往具備相對完備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以及官僚體製(此處哈爾頓參照了《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七章的觀點)🏌🏼♀️。
問題是,正如哈爾頓在書中多處強調的,由他援引的拜占庭和莫臥兒帝國的案例來看👩👩👧,能夠在比較大的疆域內達到足夠程度有效中央集權的古代國家都會面臨非常巨大的挑戰。其中最大的困難是👩🏽🏭,古代國家,尤其是古代帝國,需要大量賦稅來維持基本的行政、司法和軍事防衛,而在當時的交通🕵🏼♀️🚘、通信🧏🏻♀️、財政和轉運條件下,收取農民的剩余勞動產品🥳,無論是用勞役👨✈️、實物還是貨幣形式,都不可能像現代國家那樣,完全依靠一個遊離在地方利益之外的官僚集團,譬如一個借助教育和銓選製度而養成的帝國政府精英階層💅🏽。這樣一個官僚集團是七到十一世紀拜占庭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所管理和運作的國家財政和軍事保證拜占庭抵禦了阿拉伯人🏄🏿♂️🦻🏻、保加利亞人和塞爾柱突厥人等眾多外族持續和大規模的進犯✋🏼。拜占庭的困境是,這些皇帝官吏,在古代的經濟政治語境中🥸,自己也遲早會變成地方貴族,組成新的或者融入既有的地方利益集團,分享甚至過度攫取中央政府需要的資源,並因此削弱國力🚾,甚至導致國家的瓦解👃🏿。所以哈爾頓以及和他立場一致的學者對前現代國家都有下述基本認識🧑🏼🦱🫲🏻: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構成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而地主階級內部因為剝削所得的分配還存在另外一個復雜關系,也就是皇帝及其宮廷精英與地方貴族地主之間的矛盾。後者往往從中央政府獲得財富、頭銜和榮譽,往往通過加入官僚集團來表達自己對皇帝的忠誠🔐,同時也是皇帝不得不依靠的力量,但是他們不是單純依靠薪俸生活的現代國家官吏🏋🏿,他們在負責收取和轉運農民剩余勞動產品的過程中,更加容易把自私和短期的利益置放在國家長遠的利益之上,譬如通過兼並自由小農的土地,破壞國家的財源和兵源👯♂️🈺,並最終削弱中央政府,使之無力直接控製地方和邊遠地區🩹,無力抵禦外敵入侵👴🏿。

約1180年的拜占庭帝國地圖(來源:stephanus.tlg.uci.edu)
回到《漢興》💇🏼。李開元力圖闡釋的古代社會政治理想恰恰在於,政治權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恰當和有機的配置,地方對中央政府的高度認同和向心力,以及地方擁有相當程度的權力和治理能力,從來都是建立有效的古代中央政府統治和古代統一國家的基礎🐈⬛。而這一認識恰恰是古代文人和政治家往往不能參透和說清楚的政治思想🚛。他們也因此對直接和垂直抵達社會基層的“現代化”中央官僚體製抱有不切實際的向往——在古代落後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幾近幻想☂️。即便我們跳躍到千年之後的唐代,情況也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舊唐書》和《新唐書》都曾經描寫過唐代能臣劉晏(七一六至七八〇)在朝廷掌控地方官員的超強能力,認為他能夠洞察官吏在遙遠地方的一舉一動🧑🏻🍼。其中《舊唐書·列傳第七十三》的描寫尤其具體傳神:劉晏不讓他委任的地方官自主行事,“其部吏居數千裏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宴語💁🏼♂️,而無欺紿👩🏽🦲,四方動靜😯,莫不先知👩🏻🎤,事有可賀者,必先上章奏”。這段描述刻畫出了劉晏的獨斷專橫,卻很難讓人相信他真的具有如此掌控能力。

唐代能臣劉晏雕像(來源🪒:bing.com)
對朝廷大臣的類似描寫🥰,常見於《漢書》以來的史家筆下,折射出古代文人簡單化和模式化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貌似對各地的情況明察秋毫👊🏼,實際上統製過緊,剝奪了地方政府自主變通的能力。他們也很容易把適度放權的封建製和權力高度集中的郡縣製對立起來,認為前者有嚴重弊病👭🏼,而不能看到二者恰當結合的益處和重大建設意義🧑🏻🦲,將突出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郡縣製看作治理和安定天下的唯一良策,將古代政治思想傳統塑造成單向度的封建製批判。李開元實際上提出了,後戰國時代的意義隱現在“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的背後”👧🏼,代表著另一種政治理想,其特征是朝廷重視和賦權地方,地方高度認同朝廷,雙方之間的“政治均衡得以建立”,國家得以走上“長治久安的發展軌道”。這是一種需要自覺選擇和實施難度很大的政治理想🏡👨🏻💻,在很多時期並未由理想變成現實🙅🏻👩👩👧👧。這也是後來顧炎武在批評郡縣製弊端的時候精辟地表達出的政治理想🦻🏼:“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弊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郡縣論一》)
但是如果我們參照哈爾頓對拜占庭帝國由繁盛走向衰敗的分析🧔🏻,顧炎武的前述理想本身就包含內在的矛盾。拜占庭政府精英的興起本來就是舊羅馬元老大貴族及其後代衰敗的結果🧑🏽🦱,然而這些與皇室關系密切的新貴在取代舊貴族之後,還是逐漸將“封建”的元素加強🤞🏽,逐漸瓦解了帝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基礎。由分析剝削和分配農民剩余產品的方式入手🖌,哈爾頓針對古代世界歷史得出了一個悲觀結論:有效的中央集權只可能發生在相對狹小的地理區域♋️。也就是說👨🦰,即便是顧炎武的方案也未必可行。換言之🤫🦶🏽,在前現代國家,“後戰國時代”是否代表著一種重要的政治思想取向👩🏿🔧,而這一理想一旦付諸實踐🍄,會很容易自行解體(因為按照哈爾頓的邏輯推演,中央政府掌控下的“分權自治”遲早會變質🍡,導致地主階級內部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地方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是否因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古人一直不能夠擺脫對作為中央集權基礎的郡縣製的迷戀?不過很多古代的地主階級精英又都懂得:強化朝廷對全局的掌握能力並不等於是全面、簡單和直接地加重中央政府的財政🙆、人事和軍事權力,更不能以削弱和閹割地方政權的力量作為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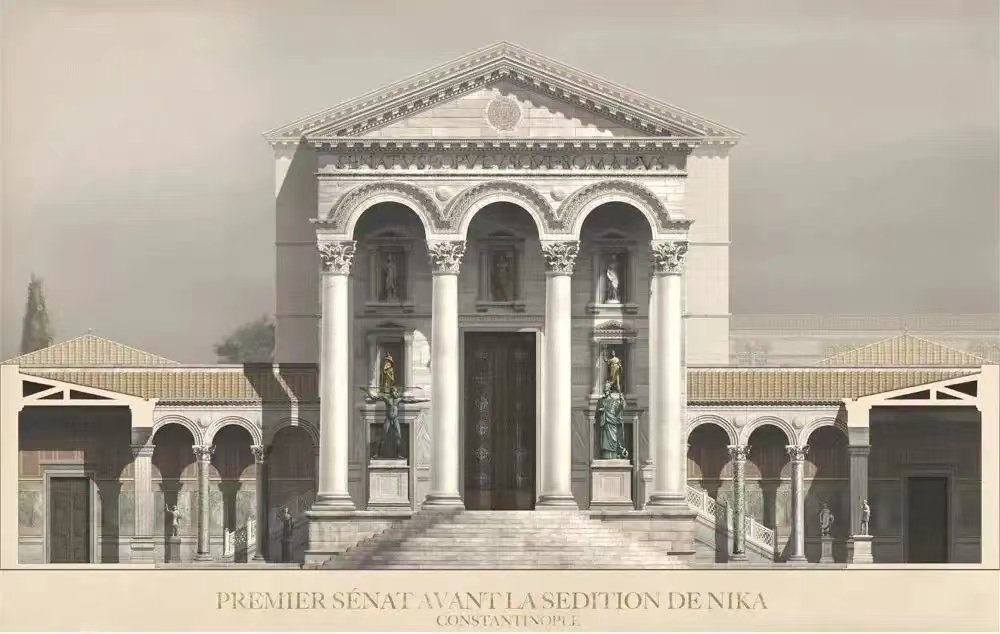
拜占庭元老院大門(來源:brillonline.com)
地主階級內部的這些官僚地主♈️,如果我們由封建社會階級關系和剩余產品分配的角度來觀察👷🏼,既是朝廷的工具,又會與國家爭利🤵♂️🥸,威脅到中央政府📧🎎。在皇帝看來,鉗製與之瓜分剝削農民所得利益的官僚地主是封建政治權力鬥爭的主要方面。那麽皇帝是否會過度伸張皇權,迷信郡縣製⛹️,打擊地方積極性🦑,自斷手足👟,最終傷害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王夫之反對皇帝聚斂財富太盛,認為“盜民而國為之乏”,會危害到整個社會(《讀通鑒論》卷二十二)。然而豪強對百姓的欺壓和剝奪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是中外古代歷史上常見的現象。皇帝與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之爭,並不是那麽好解決的🏄♀️。哈爾頓對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內部關系的解讀,應該有助於我們理解《漢興》一書所展現的古代國家、古代政治和社會關系。哈爾頓懷疑古代中央集權國家的可行性🈚️,因為他認為直接的👩🏿⚕️、單純郡縣製的統治方式在古代是很難有效的。
李開元在《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裏研究的軍功受益階層是皇權在王朝建立之初的關鍵社會基礎🤱🏽。《漢興》的一個關鍵內容就是用栩栩如生的文筆描寫了劉邦及其後人如何防止這個官僚地主集團走向反面,成為與皇室和朝廷爭奪資源和權力的危險勢力🥕。除了韓信、彭越和英布之死,在他的筆下,蕭何在當了丞相後如何設法消除劉邦的猜忌和逃脫權力的災禍,也被寫成了一個復雜的故事🧷。李開元同時也寫出了大臣們伴君如伴虎的酸楚🪰:“蕭何的一生中,與劉邦的關系最為玄妙,互相欣賞💤,互相信任,互補互助,又互相猜忌提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到頭來入獄受辱,出獄遭譏👨🏿🍳,那句‘我劉邦不過是桀紂主,你蕭何是賢明相’的怏怏自嘲之語,最是皇權官僚集權體製下非情無奈的荒唐話。”此處的“集權體製”一語👩👧👦,是否用“皇權與官僚集團相互製衡體製”替代更加合適😂?
蕭何之後,書中還寫了“蕭規曹隨”的曹參,寫了曹參飲酒高歌👩🏽🦳、無為而治這一細節🧙🏿♂️。這裏固然有曹參應用黃老之學治理國家的智慧🐨,但是李開元也借用漢代這位第二任相國來說明西漢皇權之有限和相權之獨立,說明漢代政治比秦代高明的地方恰好就在“漢高祖接受的相對有限皇權”🧴。結合前面蕭何的故事,皇權與官僚權力的某種平衡和相互製衡被理解為漢初朝廷政治的特征,並被解讀為“黃金時代的文景之治”的基礎。我們可能需要指出🤟🏿,比較和諧和平的皇權政治並不應該片面地歸因於對皇權的製約,官僚地主集團同樣是需要被製約的一方——通常在實踐中是被皇帝製約🧑🦱♧。肆意妄為的權貴,無論在朝廷還是在地方🧑🏼✈️,完全可能和昏君一樣危害到封建國家⚛️。
《漢興》的最後一章和結語應該是全書的精華🙅🏿,凝聚了作者對歷史的深度思考。作為一個強大的古代封建國家,漢代一統天下的地位毋庸置疑。這一格局與漢代皇帝分封王侯並不矛盾。關鍵在於,相權的相對獨立和諸侯在自己領地的封建統治權力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權力適度分散和製衡機製↪️,是否就一定要概括為“分權自治”和“不擾民亂民”的無為而治🎉?由社會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分析的思路去看,考慮到地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因為剝削農民所得的分配而發生利益沖突這一事實,我們是否需要強調此處的“新貴族主義”和“分權主義”恰恰是皇權與封建國家中央政府權力向下延伸並建構更加有效社會控製的手段,並最終導致皇權進一步得到加強?這樣看來🚴🏻♂️🌤,是否哈爾頓對前現代國家有效中央集權的可能性評估過低了?
二、“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
從社會控製和政治統治的角度觀察,中世紀西歐國家的有效中央集權是否並不亞於拜占庭和東方古代國家🧑🏻🦼?甚至可以說西方中古時期的君權要更加強大?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引入哈爾頓曾經的同事克裏斯·威克姆的研究。他和哈爾頓一樣是堅持使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學者。威克姆近年出版有《中世紀歐洲》一書(Chris Wickham,Medieval Europe, 2016),其中有些觀點也出現在他已經被翻譯為中文的著作裏面(《企鵝歐洲史:羅馬的遺產四〇〇——一〇〇〇》)👒。

威克姆的《中世紀歐洲》(來源👨👩👧👧:douban.com)
哈爾頓在《賦稅國家》中已經談到💆🏼♀️,中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靜態地看,具有索撒爾提出的“片斷國家”的特征(Aidan W. Southall, Alur Society , 1953),也就是在政治思想上認可甚至神聖化以國王或者酋長為首的中央政府及其政治和軍事權力𓀈,同時又允許地方權力中心分享甚至僭越這些權力。然而與索撒爾研究的非洲社會不同,法蘭克王國政治權力下沉和分散的過程恰恰使得社會控製在整體上得到了加強:封建領主及其封建城堡在西歐網格式的分布,不僅大大加重了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建造了農民的“囚籠”,而且構築了一個貼近基層、反應迅速的社會治安和軍事防衛的體系。哈爾頓沒有討論到十世紀之後的情況❎,也就沒有討論到封君封臣製度可能會有的加強王權的功能💆🏼♀️;他希望強調的是,拜占庭帝國直接任命的官僚集團曾經嬗變為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威克姆則更進一步地指出,在後加洛林王朝時代,當法、英、德和西班牙🧑🏿⚖️、匈牙利等地的國王試圖在與貴族博弈和相互製衡中加強王權的時候,封建領地和封建城堡實際上是整個社會控製機製中非常關鍵和有效的組成部分,構成了地主階級以超經濟強製向農民索取剩余產品的製度性保障,而且也是有效的行政和司法單位。他舉例說,當十三世紀中期蒙古人入侵匈牙利的時候🫴,國王意識到壓製地方貴族是一個削弱國家整體實力的愚蠢舉動,因為正是這些遍布王國各處的封建貴族控製的城堡,提供了極其有效的防衛🩶,因為據守這些城堡的貴族以及周邊的民眾具有抵抗外敵和保衛家園的強大戰鬥意誌。在這個意義上,地方積極性無疑起到了加強王權和整個國家團結的作用。

君士坦丁堡大皇宮🍧,拜占庭皇室宅邸(來源👨🏽🔧:google.com)
當西歐封建君主加強王權🫰🏽🧑🏻💻、走向近代國家的時候,他們正是利用了封建領主們在基層社會修建的一個個城堡及其周邊的微小單位🧑🏻💻,將之作為建立強大君主國家的“磚石”。近代早期西方的中央集權君主製國家正是這樣被建立在“網格化的地方權力結構之上”的。寫到這裏,我其實是想指出,李開元所討論的後戰國時代的新貴族主義和分權主義現象,確實並不一定是“分權”或者“分權政治體製”,而應該被看作建構天下大一統的另外一種有效途徑。也就是說,政治權力有效下沉到基層社會,基層社會的建設得到有效的重視🤷🏽♀️𓀊,儲富於民👪🤏,且文化思想能夠活躍輕松,如果這些能被看作統一帝國體製的基本元素⛹🏼♂️,並借助皇權與貴族的互動和製衡得到貫徹落實,那麽古代國家治理的理想境界確實可能實現和長久維持:“城邑鄉村👩🏻🦱🧴,雞鳴狗吠之聲相聞🎯,人氣炊煙萬裏連綿🍶,舉國一片和樂景象♌️。”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這是班固在《漢書》裏面對“文景之治”的簡要概括。我們解讀古代文本常常有將之現代化的傾向,譬如籠統地將漢文帝📇、漢景帝的一系列活動理解為統治者在處理與百姓的關系。而實際上👨🏿,兩位皇帝的關註重點應該更多是朝廷與貴族或地方精英之間的關系。文帝即位前說:“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這話不僅意味著他力圖取得“宮廷、政府與諸侯國間的政治均衡”,而且在更廣泛意義上,他意識到,他需要處理好帝國中央政府與地方統治者之間的關系💆🏿♀️。李開元所說的漢文帝六大歷史功績其實都深度涉及這層關系,而不是常規意義上皇帝與普通民眾的關系🐄。譬如其中廢除“誹謗妖言罪”這一法製改革。其意圖當然不是允許百姓隨便街談巷議和謾罵皇帝☄️🧔,而是說對貴族的政治言論要有寬容度🧖🏿,允許他們發表不同意見。兩漢多“庸主”👌,“漢詔多懼詞”🏡,其實很多漢代的皇帝是明君🪷,懂得如何審慎妥當處理朝廷與地方統治精英的關系,從而維護了長治久安的局面。
“封建之在漢初🧎🏻➡️,鐙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焰”(《讀通鑒論》卷二)。在郡縣製體製下👩🏼💻,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仍然是關系到古代帝國興盛與否的關鍵。王夫之註意到“漢郡吏於守義猶君臣”,認為皇帝要信任和適度放權於地方👩🏼🎨💹,不必疑懼地方官吏之間的親密團結,要允許地方社區和地方政治有自主的資源和活動空間;“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國家對內亂外患的抵禦抗擊能力才能強大,達到顧炎武所說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境界。所以後世在理論上並非不可復製“後戰國時代”,但是正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那樣,這是一項非常復雜和艱巨的工作📋。哈爾頓以為,受製於落後的交通👩🦰、通信和財政製度,古代中央政府持續有效統治一個疆域廣大的國家非常困難,充滿風險🧳,但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並非完全不可能💪🏿,其成功的最重要條件在於和諧因而堅固的政治文化認同🔐。而創造這一條件📵,同樣是非常困難和充滿風險的,是無數人曾經跋涉的漫長坎坷旅程。
由閱讀西歐中世紀政治的一點初步心得,聯想到了《漢興》🐮💇♂️。我在這裏不僅讀了開元娓娓道來的一個個故事,也欣喜地察覺到他思考多年的一些思想觀點🔂。我很高興我們有很多共識,同時還有一些小小的分歧。
原文鏈接🐕:“雖數千裏之外,奉教令如目前”——古代國家統治的理想與現實(《讀書》2024年8期新刊)
轉載本網文章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