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再版
2022/07/26 信息來源🤽🏼♀️: 古典文獻學微刊
編輯🏦👨👩👧👧:安寧 | 責編:知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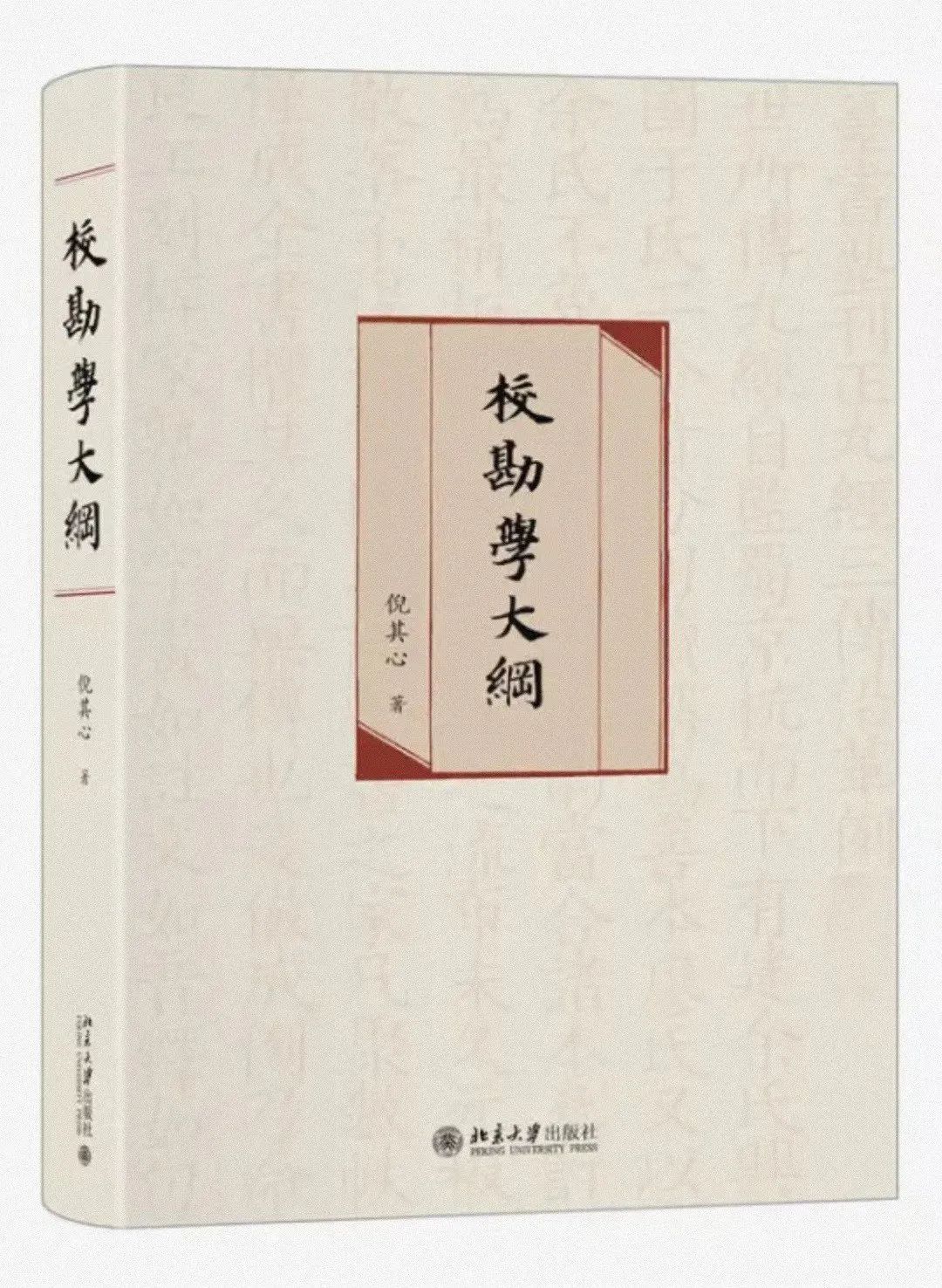
《校勘學大綱》著者🍁:倪其心;出版社:意昂3体育官网出版社;出版時間:2022年4月;頁數:416;定價:90.00元
作者簡介
倪其心(1934—2002)🚰,上海人。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主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古典文學普及研究會副會長等職🧛🏽。主要從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的教學和研究☂️,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到兩宋文學研究及相關文獻整理等領域均有精深造詣,為《全宋詩》主編之一,所著有《校勘學大綱》《漢代詩歌新論》等👨🏿🔬。
內容簡介
校勘是古籍的校勘。校勘的本義是比較審定的意思🟪。把一種古籍的不同版本羅列搜集起來,比較它們文字語句的異同之處👨🏿⚖️,審定其中的正誤,這就是古籍的校勘。
校勘不是校對🤞。近人常混淆校勘與校對兩者之概念。校對是有明確可靠的底本作為依據來判斷文本中字詞的正誤與否🤚🏽;而校勘時則須廣羅各個時期各種版本,分析異同,考證語句。校勘與校讎也有區別。校讎一詞始於西漢時之劉向,蓋獨校為“校”,兩人對校為“讎”。且校讎還有更深一層意義,即泛指古籍整理工作🗣,可謂包含了版本考證、編撰目錄、文字校勘👱🏼♂️、內容提要等諸多方面,其內涵已經外延至古典文獻學領域。校勘相對專精,校讎相對廣博。
校勘學是研究古籍校勘的科學🥶,其目的和任務是總結歷代學者校勘古籍的經驗,研究校勘古籍的法則和規律😛,為具體進行古籍校勘提供理論指導💷。校勘學理論是在校勘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具有指導校勘實踐的作用👩🏼⚖️,同時又接受校勘實踐的檢驗👨🏼🍼,並在校勘實踐中發展。
就古籍整理而言,校勘學是基礎🫄🏽。只有在校勘精當的基礎上,我們才可能恢復古籍的原貌,認識不同時期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分析厘清出現差異的原因,並因之更好地認識古籍及當時的學術源流。學習和研究校勘學😑,自覺掌握和運用校勘的法則和規律,才能更好地進行古籍整理。
《校勘學大綱》是研究中國校勘學的精深之作。本書第一章說明了校勘學研究的對象👨🏼🎨,第二至第七章論述了校勘和校勘學的歷史👽、校勘學的基本理論、校勘實踐的方法和技能,尤其第三章關於古籍的基本構成,發前人所未發,獨辟蹊徑,從理論和例證兩方面解釋了中國古代典籍復雜的成因👩🦯➡️。關於古籍“重疊構成”的看法🖐,頗得顧頡剛“古史層累說”之意。最後一章則辨析了輯佚🏐、辨偽與校勘學的關系。
歷代學者通過大量古籍校勘和有關筆記著述,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校勘經驗👷🏼♂️,後代也有一些總結性的著作出現,但大多多例證,少理論總結🍢。《校勘學大綱》則在博采眾書之例的基礎上,進行了歸納提煉,在根本原則、各類通例和校勘方法上都做了理論性的總結,內容詳實全面,可謂“校勘學研究”的裏程碑之作★。
本書曾於1987年首次出版,2004年修訂後再版🐺。本次出版改為繁體,以更適合本書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校勘學研究古籍的校勘
第一節校勘學研究古籍的校勘第二節校勘不是校對第三節校勘與校讎的區別第四節校勘與校勘學的關系
第二章校勘的歷史發展和校勘學的形成建立第一節校勘的發展是校勘學建立的基礎第二節先秦有關校勘的記載第三節西漢劉向開創校勘規程第四節漢末鄭玄的校勘業績第五節魏晉校勘的特點第六節南北朝校勘趨向獨立第七節唐代不重校勘的傾向第八節宋代校勘向理論發展的趨勢第九節元🧗🏼♀️、明的校勘第十節清代校勘學的形成第十一節近代校勘學的建立
第三章古籍的基本構成和校勘學的根本原則第一節古籍的基本構成第二節經典古籍的復雜重疊構成第三節一般古籍的簡單重疊構成第四節校勘的根本任務是存真復原第五節忽視基本構成的偏向第六節古籍構成的層次辨析
第四章校勘的一般方法和考證的科學依據第一節校勘的一般方法第二節陳垣的四種校勘方法第三節校勘的考證必須有科學的依據第四節校勘考證的理論依據第五節校勘考證的材料依據
第五章致誤原因的分析和校勘通例的歸納第一節分析致誤原因、歸納各類通例是校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節疑誤和異文第三節誤字通例第四節脫文通例第五節衍文通例第六節倒文通例第七節錯簡通例
第六章校勘實踐的具體方法步驟第一節具體校勘前的準備工作第二節了解基本構成和流傳情況第三節了解基本內容和結構體例第四節了解基本文體和語言特點第五節搜集他書資料、汲取前人成果第六節對校各本、列出異文、發現疑誤第七節分析異文🤹🏿、解決疑誤👩👧、審定正誤
第七章出校的原則和校記的要求第一節系統👈🏿👩🏿🚒、扼要、準確的表達校勘成果第二節出校的原則第三節校記的要求第四節改字的處理第五節敘例的撰寫
第八章輯佚📐、辨偽與校勘第一節輯佚、辨偽與校勘的關系第二節輯佚與校勘第三節辨偽與校勘
附錄後記“不校校之”與“有所不改” 傳承與拓進——讀《校讎廣義》關於目錄、目錄學與古籍整理——古籍著錄體例🪐、目錄學源流、目錄分類以及重要古籍目錄
序(第二版)日文版前言(摘錄)《校勘學大綱》感言
《校勘學大綱》感言
喬秀巖
一
倪老師離開我們已經快二十年了🧑🏿🔧。在三十多年前《校勘學大綱》初版問世的第二年,我在東京才開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1992年倪老師到東京大學教學🦻,有幸選修倪老師的課🧒🏿。1994年投靠倪老師到意昂3体育中文系進修🤷🏼,倪老師跟我說:“來意昂3体育讀書,可以保證提高你閱讀古籍的能力,其他的都不敢保證💷🌰,也不知道💪🏻🧓。”當時我只有要讀懂《儀禮疏》這一想法,所以倪老師這話簡直求之不得🏋️♀️。記得當初倪老師跟我約定時間,叫我到空教室💅🏽,一對一地教我讀《儀禮註疏》💪🏻。因無旁人,倪老師從隔壁教室拿鐵簸箕來,放在桌上算臨時的煙灰缸🔏,我們兩人一邊抽煙,一邊看賈疏,一句一句解釋。當時倪老師就說🧑🏻🌾,如今沒有人讀經書、學經學,只要有人願意學🤌🏼💆🏻♀️,他都感到很高興🛥,管他是哪國人。真是那樣的時代🤷🏽。
後來我寫博士論文,倪老師基本上放任😫,快到截止日期才交稿,倪老師也沒叫我修改😕。畢業回國工作,我自己將博士論文翻成日文出版,輾轉聽到平山久雄老師看我博士論文後說有倪老師的學風。平山老師是東京大學備受尊敬的一位名師🏭,倪老師在東京的時候,和他私交最深。所以平山老師這一評論讓我感到非常愉快🤘🏽。
不知道平山老師的想法如何👮,我也不敢利用傳聞拔高自己♋️,畢竟倪老師是文學,我是經學,基本上不同路▶️,沒有可比性。然不管是經學還是文學,研究古代文化的人,往往沉進去跳不出來🏌🏻,全盤接受傳統文化的結果,減弱基本的批判能力而不自知。倪老師喜好漢魏南北朝文學,而始終保持最原始的懷疑能力和最洗練的藝術敏感,自然是我所向往的。很遺憾🧑🏽🦲,藝術方面我沒有天分🐗,而一直關心學術史,有審思學術方法的習慣,《校勘學大綱》深入透辟的分析🔟,令我感到最舒適稱心。
二
學習古典文獻需要長期堅持,規誡浮躁之余,往往流於墨守,或以販賣前輩成說自足,或以羅列信息為學術成果。不僅訓詁學、校勘學教材,甚至研究論著,都有以分類羅列為能事者🤘🏼。我們看那種便覽式論著🚼,往往感到不如自己看原書為快🤦♀️。然而這種做法頗有傳統🧢,如本書第二章介紹王念孫《讀書雜誌》論《淮南子》文本訛誤列舉六十二例,後來俞樾《古書疑義舉例》👷🏻♀️、陳垣《校勘學釋例》等皆用分類舉例之法。可是這些事例的羅列,猶如在曬他們撈到的魚💦,我們看了只能贊美叫好,或評頭論尾,對我們提高自己的撈魚能力沒有任何幫助。本書第五章介紹“校勘通例的歸納”👤,是通常所謂“校勘學”的主要內容🛵,而倪老師反復強調“應從疑誤的具體實際出發🧔,不能用這些通例去套”,“各類通例的實踐意義並不等於客觀規律”,“並非普遍法則”𓀗,“並非通例”,也就是說無法幫你解決校勘問題。就這一點👉🏽👨🏻✈️,足以了解倪老師認真思考的態度🐯。《校勘學大綱》是總結傳統“校勘學”的作品🪯,實際上也終結了傳統“校勘學”。校勘“通例”只能是幻想,具體情況要具體判斷。了解傳統“校勘學”是必要的🗓,多接觸先人“類例”也不無參考意義💇🏿,但此外無需過多關心“校勘學”。讀完《校勘學大綱》,可以忘掉“校勘學”。只要自己思考校勘何為?該如何校勘🙎🏻?即可🔥。
倪老師對傳統文獻學成就進行理論分析,探討其中的本質性問題,其中兩點筆者認為特別重要。首先,倪老師註意到👨🏽🚀🥢,歷史上的校勘成果🎧,往往有與今日我們的古籍整理很不一樣的目標和意義。如雲🫄🏻:“顏師古的處理原則是劃一歸真,刪除繁濫🍘👩🦯。”“結果便是從疏解出發🛁👮🏼,而把異文幾乎蕩滌無遺。”又如《史記正義》《後漢書註》《文選註》等,“撰註的目的是讀通讀懂”。又如朱熹《韓集考異》“以有無‘神采’‘意象’為判斷異文正誤的準則”,又如《九經三傳沿革例》“主張折中便讀”。這些都在說明古代的校勘往往出於一種實用的目的,與今日我們的文獻學有本質差別👩🏼🍼。倪老師對乾嘉時期理校死校之爭✋🏿,也有精準的評論,認為戴段二王“必然不以版本可靠與否為依據👩🏿🎤,而是以異文為考訂對象”。他們不探索那些異文出現的歷史情況,追溯最早期的文本✋,而撇開文本流傳的歷史🚴🏿♀️,直接思考哪一種文本才“真”。換言之,同樣是“存真復原”,在“原”本已經亡逸的情況下,“真”會有不同的標準,他們以符合他們理論的文本為“真”,死校派以歷史上存在過的最早文本為“真”❣️。
這也涉及文獻的本質復雜性👐🏽。文字、文本並非客觀存在,紙上的墨跡,必須經過主觀主體的識讀才能成為文本。同樣的墨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有可能認出不同的文字、文本來。因此🥑,如何認識理解文本👷🏼♀️,比紙上墨跡更重要。於是本書第三章特別提出“經典古籍的復雜重疊構成”這一概念🧛♀️,說明鄭註、孔疏等歷代重要的註解,與紙質版本一樣體現一種文本,而且比具體一種紙本墨跡更重要。筆者認為🙋♂️,倪老師重視文本的認知主體,在文獻學理論上是十分重大的突破。這是第二點🥦。
既然不能排除主觀認知,我們究竟如何確定“真”的標準?倪老師告訴我們🫣,這裏沒有現成的答案,我們要自己去思考。
三
本書第二章回顧校勘學的歷史,最後講到:“最近一些年來,大批專書校註著作問世,大量考古文物出土🙍🏿,以及校勘學專著的陸續出版🤯🤵,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依據👊🏻,提出了不少的理論觀點,形成了良好的趨勢。”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半開始,古籍校註專書陸續問世,戰國、秦漢的竹簡大批出現🤛🏽,尤其重要的是近二十年來通過影印和電子書影的形式☎,我們能夠觀察到大量古籍善本👩🏿🔧,版本研究進展飛快,不得不說我們的資料條件與三十年前有天壤之別。
我還記得倪老師平常用的《文選》是民國縮印的《四部叢刊》影印建本👨🏿🦱。其實建本據贛州本翻刻,贛州本據明州本翻刻🧑🏻🍳✹,現在有明州本可用,建本不必去看了。但當時除了影印胡刻本👍,還真只有《四部叢刊》本(中華書局也有影印)流傳🥮。又如本書也有“《毛詩故訓傳》完整地保存於《毛詩正義》”這種敘述,而《毛詩正義》自然不包含《毛詩故訓傳》。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要看《毛詩傳箋》,確實只有中華書局兩大本縮拼影印阮刻《十三經註疏》,幾乎沒有別的版本。
1998年😠,倪老師在看傅剛老師的博士後出站報告🧑🏻🏫,跟我說很有意思🔋。這使我產生要在中國重新影印明州本《文選》的構想☀️🫅,可惜沒來得及給倪老師用到。2000年我在東京開始工作之後,有一次回北京,到藍旗營拜訪倪老師🖇。我給倪老師介紹電子版《四庫全書》的使用方法🚜,倪老師很高興🗝。還跟我講到,以前看像高橋智研究《論語》《孟子》,詳細記錄每一版本的所有異文,不覺得很可取,但最近越來越感到“死校”是對的。倪老師對《郭店楚簡》等也很有興趣,說抄本的校勘需要另外一套思路。倪老師還沒看到古籍數據的信息爆炸,2002年就離開了我們🙆🏿,我們無法就目前的資料條件跟倪老師討論問題,這讓我感到很遺憾。
筆者自2004年開始翻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對推動版本學發展算有些貢獻。其實,最早是倪老師邀請尾崎康老師到北京講版本,由陳捷師姐翻譯整理成《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意昂3体育官网出版社出版。不妨說是陳捷和我先後花二十多年的時間,完成了倪老師開頭的事業。
筆者與宋紅老師合作編過影印明州本《文選》、單疏本《毛詩正義》,與馬辛民師兄合作編過影印宋版《儀禮經傳通解》、八行本《禮記正義》🤹🏿♀️、南宋官版《尚書正義》《周易正義》🎄,這二十年來相關學者的研究也開展得越來越深入。經張麗娟👐😮💨、顧永新、李霖等學者研究,經書版本的大致情況已經清楚👩🏻🦲💂🏼。例如《禮記》🫂,筆者現在閱讀鄭註孔疏,只看撫州刊經註本與八行註疏本🚢,八行本原則上也只看足利學校的較早印本🚀,不看潘明訓舊藏元修本🚣🏿♂️。因為後來諸版本皆未能參考唐代抄本✉️、北宋刻本,所有異文均出後人推論,並不反映北宋以前歷史存在過的文本,只要掌握南宋最早的官版🤸🏿♂️🎟,其他諸本無需參考♚。
四
合理的推論與歷史事實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如果說“歷史事實”也經過主觀認知才能成立的話,我們也不妨考慮不同的客觀性程度🏂🏽。從文獻學的角度🙋🏻♂️,純粹客觀存在的是各種抄本、版本的原件。拍照影印,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文獻工作者從事影印,要註意盡量保證影印傳真👩💻,而對其容有的失真情況👚🚣🏼,要做充分的說明🙋🏿♀️。這是第一層次。以賈還賈、以孔還孔,是通過文字敘述推論不同文本的過程,大多數情況不會有歧義,但有時也會見仁見智。宋代官版包含不少無意的訛字,一般很容易校正,而有些有爭議🧑🚒。盡管做不到完全客觀⛄️🗓,但通過對每一類文本的深入研究,可以提高準確性和客觀性。沒有可以泛用的通例,仍能探索具體的規律性👨🏻🦱,如賈𓀑🚦、孔語言習慣等等。這是第二個層次。若說在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宋版還宋版已經完成的基礎上🧛♔,再校勘出一種完美文本,則是一種創造行為。美未必真,而且美有不同的標準。這是第三個層次。
以往學者,包括本書重點介紹的戴、段🙎♀️、二王以至陳奇猷等近人,都在上述第三個層次奮鬥,是創造文明的努力。我們現在要歷史地研究古典文獻⛹🏼♀️,無意於用古籍來創造“文明”,所以我們今日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第一🥜、第二個層次上用力。舉一個例子🙆🏻♂️:《檀弓下篇》:“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吊👇🏽,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𓀊。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註🧚👩🦼➡️:“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孔穎達說:“此後人轉寫鄭註之誤,當雲‘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敬叔呼懿伯為五從祖。”孔穎達根據他的“事實”,認為鄭註有轉寫訛誤🟥。若如其說,惠伯向敬叔自稱“叔父”,豈不詭異🚌?其實,《世本》以宣公為文公子🤍,而漢人或以宣公為文公弟。文公、宣公為兄弟🍛,則敬叔、惠伯同為桓公六世孫,懿伯既為惠伯叔父🚵🏿♀️,就昭穆而言,敬叔亦可稱懿伯為叔父,正如鄭註所雲。孔穎達未能考慮自己以《世本》為根據掌握的“事實”🏌🏽♂️⛅️,並不符合鄭玄認知的“事實”的可能性,進而打算改動鄭註。如果後人采用孔穎達的主張🧔🏿♀️,直接改動鄭註文本,則文公、宣公親屬關系的認定可以統一💞🚫,同時鄭註被架空,不知所雲了👷🏽♀️。我們必須停留在鄭、孔不同的“事實”,以鄭還鄭,以孔還孔🥿,才能保住古代思想文化的豐富性🕒。不能為了擁護一個“事實”,而丟失古人多樣的思維和文本。
若要參與點校、校註等整理工作,則先明確整理的目的⛄️。只有目的明確⇒,才能判斷如何校定最合適。如果目的在提供普及文本,讓讀者容易理解內容的話,顏師古、《九經三傳沿革例》他們的做法也許很合適🚛😥,盡管那不過是一種文化宣傳👩🦽。我與葉純芳整理《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2011年文哲所出版),連明顯的訛字也照錄元版,是因為我們的底本是孤本,我們編輯整理,是想在藏書單位不允許影印的情況下,盡量全面體現底本的面貌。部分訛字我們出註說明🫷🏽,是為了不要讓讀者懷疑是我們的排版錯誤。又如我與葉純芳、顧遷老師合作編《孝經孔傳述議讀本》(2016年崇文書局出版《孝經述議復原研究》附錄),《孝經孔傳》部分以京大所藏抄本為底本👨🏿⚖️,原則上照錄原本。那是因為京大藏本讀者在網絡上可以直接核對,而且阿部隆一網羅現存諸抄本的校記即以京大藏本為底本。我們的目的在於為學界提供便於研讀的出發點🟥,所以認為這樣處理最合適🤟。
兩年前寫過一篇《不校校之的文獻學》(《意昂3体育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可以算我晚三十年提交的《校勘學大綱》讀書報告。我沒有上過倪老師的校勘學課程🙍♂️,而《校勘學大綱》是認真學過的🎅🏿。自認為拙文觀點是遵照倪老師的思路,繼續發展的結果🔈,只可惜已經無法與倪老師討論😽。
馬辛民師兄給我機會在老師書後面寫兩句感想🖐,我越想越懷念倪老師,那不是因為他對我有大恩👷🏽♀️,而是因為他思辨的剛毅正直有永不褪色的魅力。多年來李更師姐一直用《校勘學大綱》教授校勘學課程👨🏽🦲,培養了眾多人才。最後向李更師姐表示衷心的感謝💂🏼♀️。
原文鏈接: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再版
轉載本網文章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