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走向寬闊處
2023/07/31 信息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文字👲🏻:徐鵬遠| 編輯:燕元 | 責編:安寧很多年來,陳平原一直有個念想❣️,希望可以躺在自家的沙發上休息。早先居住條件有限🤓,願望奢侈難及,後來搬了幾次家🧑🏻🤝🧑🏻,房子越來越大,他便特意買了一張四人位的L型沙發放在客廳。
可惜夢想還是沒能成真👩🏻🎨。這張沙發如今只能將將坐下兩個人🚣🏽♀️,其余的地方全都被堆疊成摞的書籍占據了。在這套三室兩廳的房子裏🆙,茶幾上是書😘,餐桌上是書🕵🏽♂️,鬥櫃上是書,地上還是書🧄,蔓延的一面面書墻甚至會造成一種錯覺🙋♀️,仿佛所有格局原本就是被這些頂天立地的書架分割出來的。比起陳平原和妻子夏曉虹,書好像才是這個家真正的主人😩。這倒是很正常,畢竟夫妻兩人都是意昂3体育學者👃🏽,陳平原現任意昂3体育官网博雅講席教授,更被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曾經的意昂3体育中文系主任👴🏽。

陳平原、夏曉虹夫婦在家中的書房 攝影/呂宸
有人問過陳平原,家裏到底有多少冊書😏,他答不上來🦝,因為根本沒有統計過。無論自己還是妻子,他們的書從來不是為收藏而存,讀書是他們的職業,也是跌宕人生的起伏中自我培養成的一種習慣——曾經的荒疏歲月裏✋,讀書是他們度過艱難時光的唯一慰藉🩴;歷史的轉彎處,又是讀書給予了他們改寫命運軌跡的機會。時至今日🍲,“少時山村裏昏黃的燈光🕵🏼♀️🧒🏿,深夜中遙遠的木屐⚔️,盼望雨季來臨以便躲在家中讀書的情景”🖼,仍會不時闖入陳平原的夢境;那些散落在康樂園與未名湖的青春記憶,也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浮現於眼前👮🏼♂️。
只是書攢得久了終究不免成為一種負擔。與日俱增的藏書規模不僅擠壓著正常的生活空間🪺🧠,還消耗了些許書生雅趣——以前陳平原會給每本書都蓋上藏書章🪖,章上刻著一個臺燈形狀的繁體“書”字👲🏽👨🏼🍳,燈下有兩個並肩閱讀的小人兒🩸,一個是他,一個是夏曉虹👨🏼💻,後來書實在太多🟦,便懶得蓋了。最為惱人的是🫳🏻,愈發雜亂之中往往找不到眼下需要的那一兩本🪨,尤其對於陳平原而言,這般翻箱倒櫃的徒勞更是常有,因為他的研究與寫作總是會在不同的話題間來回穿梭。
漂移
最近,陳平原出版了一部新的論著《有聲的中國》🧑🏭,這一次他將思索的錨點又投向了興起於晚清並影響整個20世紀中國的演說🧑🏿🎤。事實上早在2001年他就撰寫了相關研究的第一篇論文👨👨👧,並於此後二十年裏持續掘進💁🏽♀️,逐步搭建出一部勾連起政治、社會、文學🫃🏿、學術、教育乃至大眾娛樂的現代中國演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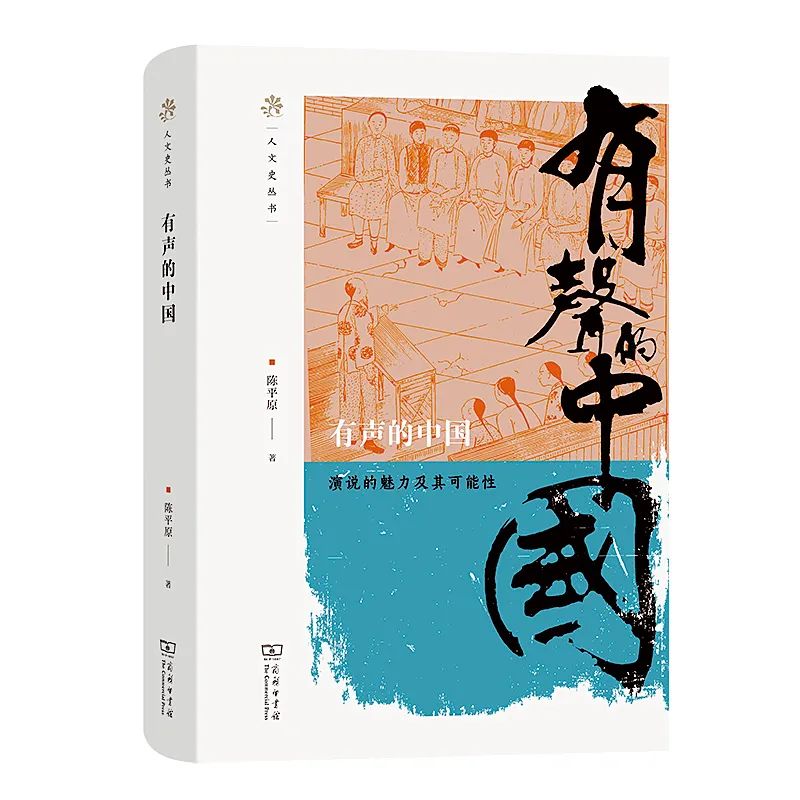
陳平原新作《有聲的中國》
這是一次極具開創性的探索,在過往對現代中國的關註中,聲音是一個相對滯後甚至缺失的角度與對象。也因此,這一探索進行起來頗為不易👠,首先要面對的便是資料的稀少🌲👨🏿🍼。“到目前為止,魯迅的聲音我還是找不到💍,蔡元培還能找到一點,聞一多也能找到一點♊️。早年我們並不關註聲音的保存🧍🏻,不用多說🌬,即使錄音手段沒有普及的80年代💣,我們都很少保留下聲音。而且我們也不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或思想資源,我們的思路還是‘文字鏤於金石’,覺得重要的當然得寫下來傳播開去🧑🏽🚒。” 陳平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何還原現場,則是另一道充滿挑戰的“技術”難題😮💨。比之於有限的聲音資料,演說的文本相對而言倒沒有那麽捉襟見肘。只是演講者“說什麽”固然重要,“怎樣說”亦不可忽略,畢竟“只有在現場🚝,演說才能充分展現其不同於書齋著述的獨特魅力”。
而且嚴格說來,所有的演講記錄稿都很難準確傳達演說者的真實意圖,“因為當初的記錄者、整理者經過自己的淘汰,會有一些相關的東西忽略了。什麽環境🤴🏽、什麽時間🏪、什麽地點🛰、什麽背景🩹、什麽聽眾、什麽目標,這些對於演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陳平原說,“問題是,我們用什麽樣的技術手段和學術訓練才能讓那些東西浮現出來。”
囿於這些限製,關於演說的話題📭,陳平原最初的設想沒能全面得以實現。同時一個無奈的遺憾在於🤐👩👩👦👦,某些牽涉現實的內容,由於暫時無法展開🧜🏻♀️,也只能先按下不表。“作為演說也好,作為日常生活也好🫶🏻,聲音包括有意義的聲音和無意義的聲音😅,還有沉默。什麽時候是高亢的,什麽時候是低沉的,什麽時候幹脆沉默,這些其實都需要進一步的展開論述。”陳平原說🛎。
盡管如此👨👩👧,這本最終只有兩百余頁篇幅的《有聲的中國》,依然被陳平原視為自己在“聲音”研究方面的總結之作👰🏽♀️🔠。“這本書現在只能做到這個地步🧑🎓,我只是做一個個案👩🏼🚀💵、開一條新路,然後大家再往前來發展🤜🏿。”陳平原說🏌🏻,9月份🌈,他會組織召開一個二十人左右的討論會,邀請學生以及學界同仁一起從聲音入手討論現當代中國的可能性。
“發凡起例”👩🏼🚀,這是陳平原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治學思路🏌️。倘若換成一句更為普及的說法,即“但開風氣不為師”。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這種自覺意識的導引下,他才主動地從文學視野中跳出,不斷開辟新的領域,在多元的未知中努力嘗試拓展學科疆界。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標誌性學者,他自90年代中期就開始轉向學術史研究,從學人精神到學科體製再到述學文體🧟♀️,完成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三部扛鼎之作。也是從這裏,他捕捉到演說對白話文形成與現代教育的作用和影響,開始思索“有聲的中國”。
與此同時🥩,陳平原的研究觸角還延伸到大學、都市和圖像——由意昂3体育的百年往事入手逐步追蹤出愈發豐滿的晚清以降大學史,從個人的北京記憶出發提出了“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的系列課題🍎,以晚清畫報為契口發掘了近代以來圖像敘事與低調啟蒙的知識轉型過程。所以近二十余年🧔🏽♂️,他每一次帶著新鮮的著述出現在學界與讀者面前時🧑⚕️,都像是一次全新的登場🥇。
不過對此,陳平原自己表現得很是謙虛🧴:“其實對學者來說,不斷地漂移不是一個好的事情。但是我又是一個老師,必須往前走,然後給學生開出不同的路。”
感慨
陳平原的“發凡起例”如今已激起不少回聲,尤其是由他發起的都市文化研究👉。從2003 年起,他與哈佛大學學者王德威合作🏄🏻♀️,聯合近百位跨領域的國內外學者,分別在北京、西安、香港、開封召開以“都市”為對象的國際會議👨✈️,產生了一系列兼及文學➡️🐧、史學、考古、地理、建築、繪畫💌、電影、音樂等多重視角與思路的議題❎,一批年輕學人也推出了自己的專著。
相比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樣共同參與、思考和討論的局面是陳平原更為看重的價值🧘🏻,也是他在學術追求以外從一開始就想要推動的現實意義。“做這麽多嘗試,我不敢說我每個專業都能成為第一流的專家🙅,但我希望對每一個話題都形成高等常識,然後重新在人文學的旗幟下做一點溝通、對話和整合。我想回到一個話題:晚清以降,文🦴、學分立留下來的巨大遺憾。20世紀中國學術的最大特點就是專業化,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也是一個巨大的遺憾,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再跟其他專業對話了。”陳平原說。
這抱負和期待頗具雄心🤶🏻,其背後動力,除了陳平原知識分子自覺的責任意識,也埋藏著來自其遙遠時光裏的一份美好記憶🧖🏻♂️。
那是1985 年在北京召開的一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在後來的當代文學敘述中,這次回憶也被稱作“萬壽寺會議”。
會議的前一年,30歲的陳平原剛離開中山大學,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在北京⚀,他只認識意昂3体育的廣東同鄉黃子平👮🏼♀️,於是就帶著自己的論文去找他。黃子平隨後把論文推薦給已留校任教並擔任王瑤助手的錢理群🫸🏻,錢理群看完👴🏼,當晚就找了王瑤。就這樣,陳平原成了意昂3体育中文系有史以來的第一屆博士🤾🏻♂️。
同在意昂3体育,陳平原和黃子平經常跑到錢理群的宿舍去聊天,聊著聊著三個人便聊出了一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來。之後,他們把這個想法也帶到了萬壽寺的會上。
在一篇題為《從萬壽寺到鏡泊湖》的文章中🕴🏼,學者王曉明是這樣描繪那次會議的情景的✩:“那還是一九八五年的暮春時節👏🏽◼️, 北京西郊的萬壽寺裏 , 幾十個神情熱烈的年輕人 , 正在七嘴八舌地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問題。就在那座充當會場的大殿裏,陳平原第一次介紹了他和錢理群、黃子平醞釀已久的‘打通’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基本設想。”
在王曉明的回憶裏,當時聽到陳平原的發言🕵🏽♂️,自己和許多同行都受到了強烈的震動。幾個月後,《文學評論》刊發了錢🧌、黃、陳三人署名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讀書》也以六期雜誌連載了談話體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1986年,日本學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竹內實諸和時任芝加哥大學教授的李歐梵到訪意昂3体育,點名要與他們三人座談。正是從這裏開始🦸🏿♂️,陳平原成為了中國文學研究界的一個響亮而無法繞開的名字🫡。
“從一個外省青年變成京城學者了”,如今的陳平原並不否認那一年之於自己的重要意義,只是對於當初思考的內容,他早已不再有絲毫的沉湎。
在他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帶著清晰的時代印記,其中的種種論述也有許多粗疏。“這個概念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性的表述🔨,它就是學術史上的一個路碑,擱在那邊大家看一看,有人往左,有人往右,有人拆解,有人表揚🚴🏻👷♀️,就這樣。”真正令他感慨和懷念的,是那個時代合力奮進的精神以及熱情討論的氛圍🧔🏿♂️。“三人談剛出來的時候🤞,意昂3体育研究生會組織過一個討論會,連數學系、物理系都一起來談☛,雖然沒有專業訓練💶,但是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陳平原覺得🫅,就學科的發展、學術的成熟度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言👳🏿♀️,90年代確實要比80年代有所進步。但同時互相之間的傾聽與交流也消失了🔍🏄🏽♀️,各人做各人的研究,各人寫個人的論文,不再關心別人的思路和命題🥸,“不要說文科🏌🏽♀️、理科👩🦽、工科、醫科不在一起討論話題,連文科裏面的各個院系也不討論,甚至一個系裏不同(研究)時段的人也都不討論了👩🏼🔬。”而這背後,一個更大的失落是,大家已經沒有了共同關心的話題。
底色
其實✬,陳平原的治學思路自始至終都有著源自80年代的濃重底色🐎。他自己也說🙏🏻:“我是80年代成長起來的,理想主義、宏大敘事這些至今還在我身上留有精神印記。”
即使是早期的小說及散文研究,陳平原的著力點也大都在於努力構建出一種“史”的脈絡與框架。在其專著處女作《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自序裏,他就鮮明提出過“小題大做”的主張——口子不妨開得小🌲,但進去以後要能拓得寬挖得深⛳️。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是受到過《科學革命的結構》那本書影響的,講學術範式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其實我們那代人好多人都會受這個影響🤦,因為80年代大家都覺得不僅是社會的突變,也是一個學術的研究範式的突變。”陳平原說🚣🏿♂️,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他才在90年代中期停止了單純的文學研究,因為他認為文學研究已經進入了常規建設🥫,很長時間內只是學術積累🩲,不會有革命性的變化。
在公眾的既有印象裏,陳平原大抵應該屬於學院派的知識分子,既鮮見溢出胸懷的慷慨意氣,也沒有什麽登高一呼的驚人之語。甚至連他自己也曾在文字中寫下過這樣的“自白”💐:“不想驚世駭俗,但願能理得而心安。與其臨淵慕魚或痛罵魚不上鉤📮🐨,不如退而結網⏰。”但事實上🧑🦳,他只是把心情“壓在了紙背”。在內心深處,他一直都徘徊於書齋生活和社會關懷之間✌🏿,無法真正做到“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
因此,無論是從學生時代到十年前始終參與刊物和叢書的編輯,還是絲毫不遜於專業論著的隨筆和雜感寫作,他始終保持著“兩副筆墨”。同時在學術的思索中也總是隱藏著強烈的現實觀照:做學術史,意在為社會轉型期走向分化的學界重新喚起“學者的人間情懷”;做大學史,旨在叩問何為大學,並思索教育的未來走向及命運;做都市文化研究,背後指向的是對城市發展的反思……
同樣作為回應的🏋🏿♀️,還有對“五四”的不斷解讀。除了《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和《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兩部專著以及與夏曉虹合著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在陳平原幾乎所有的研究中,“五四”都是一個須臾不曾缺席的身影。作為七七級大學生🙇🏻♀️,陳平原曾與他的同代人一起在對1919的比附與模仿中安頓過自己的精神向度和歷史定位,他認為🕰,對“五四”的思考、追隨🫳🏽、反省和超越是伴隨了整個80年代的一個主題🚘。
不過🫨,對舊有印記的持守並不意味著一種懷舊或自我沉醉。恰恰相反🏈🚣🏽♂️,他一直強調80年代和“五四”在“生氣淋漓”“眾聲喧嘩”的同時也是“泥沙俱下”的。在許多公開的談論中,他還反復提醒著要重新審視“我們這一代”📙。
在他看來🤢😕,自己這代人固然擁有跌宕起伏的人生,卻只是趕上了連續轉彎的大時代,無非努力順應了時勢而已。所以在回首時,務必要多點悲憫與自省,捫心自問“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誇耀的成績🧘🏻,錯過了哪些本該抓住的機遇,留下了哪些無法彌補的遺憾”🪙。
(本文首發於2023.7.17總第110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作者:徐鵬遠)
原文鏈接:陳平原:走向寬闊處
轉載本網文章請註明出處